【讲义文稿】家庭农场组织化经营主体生成的制度场域[摘要]从政府、制度和组织三个维度不仅可以解释我国农业发展的轨迹,还可以解释当前家庭农场组织化经营主体生成的内在逻辑。政府供给制度是基于实现政府收益最大化的现实需要,政府推进制度创新是基于保证政府实现增量收益最大化的内在要求,通过制度创新,催生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,不只是推进政府收益最大化的方式,更重要的是实现政府与社会收益的相互均衡,以保证制度生成并发挥应有的效能。[关键词]家庭农场;组织化经营;制度场域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变迁与制度安排直接相关,政府始终是制度供给和制度监管的主体,制度生成是政府与市场主体利益博弈的结果。如果制度安排只能保证政府实现收益最大化,而不能保证社会增量收益最大化,就会直接影响政府收益最大化的持续[1](P20)。我国农业集体化经营制度保证了工业化的实施和政府收益的最大化,当这种经营制度不能为政府带来增量收益,无法保证政府收益最大化的可持续时,政府就开始推动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变迁,从而释放农业劳动力等生产要素[2],激发农民开展多种经营的活力,有效地实现了政府和农业部门增量收益最大化。但随着经济市场化、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推进,小农家庭分散化的农业经营方式逐渐显现出与市场对接的困境[3],政府着力推进农业以家庭为基础开展多种经营的政策和制度调整,同样是为了保证政府和农业部门的收益最大化和增量收益最大化。政府供给农业制度的动机在于政府收益实现最大化的现实需求,政府推进农业制度创新基于实现增量收益最大化,以保证政府收益最大化的可持续。在我国农业制度变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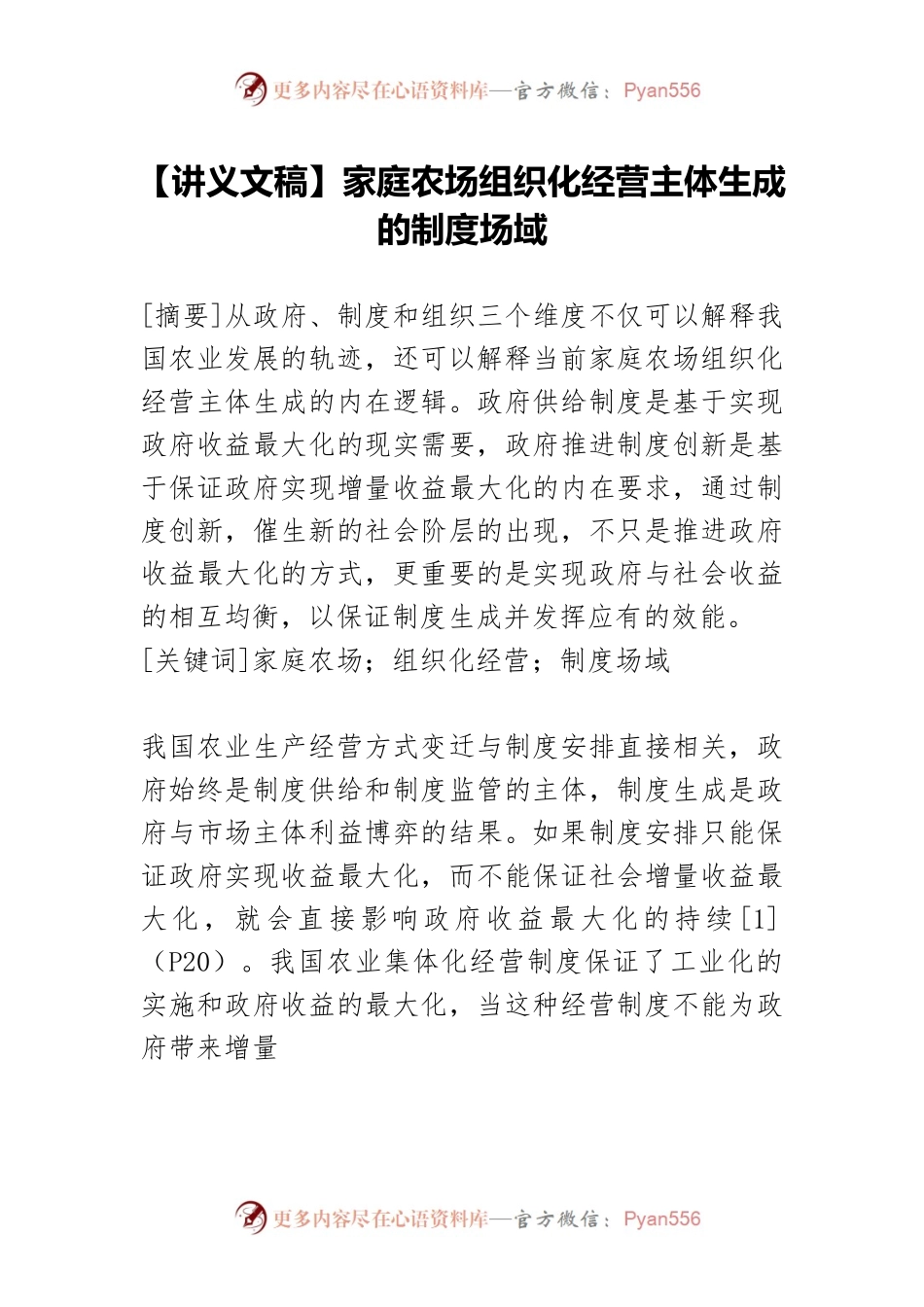

 优质
优质 优质
优质 优质
优质 优质
优质 优质
优质 优质
优质 优质
优质 优质
优质 优质
优质 优质
优质